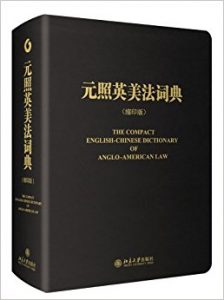- 用心翻译每一天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电话:021-58446796
公司QQ:732319580
邮箱:daisy.xu@easytranslation.com.cn
网址:www.easytranslation.com.cn
地址:上海浦东金桥开发区金豫路700号6号楼1楼
作为一家法律翻译公司,我们在翻译合同文件的过程中,深知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在界定合同双方义务和责任方面的重要性。所有的法律翻译译员都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古训来警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为确保术语的专业性和准确性,我们的译员和校对人员会使用各类法律专业词典,其中在完成英译汉翻译任务时,我们使用较多的就是《元照英美法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是我国第一本全面介绍英美法基本制度方面的词典,它在概念上填补了我国法律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本词典的编撰耗时数十年,凝聚了大量法律专业人士的心血。《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背后是一群默默无闻、埋首工作的法律研究人员,其中既有代表人物薛波,也有众多垂垂老矣但仍然秉承学术精神的法律专家。这本词典中的每一个词典和每一个释义都凝结了他们的心血并体现了他们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作为翻译工作者,这些词典编撰及翻译人员为我们树立了 一个良好的榜样,并亲自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严谨治学态度。正是这群热爱法律并胸怀理想的法律人士的坚持,我们才有幸在今天获得如此有份量的专业法律词典。以下文章摘自:唐律疏议:“薛波和他的《元照英美法词典》 (一)“对法律的初学者,我头一条建议,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请教它。”—— 哈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 1993年,29岁的薛波还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然而他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阅读外文书时,书店、图书馆都找不到好用的法律英语工具书,勉强用一本,由于都只是简单的对译词形式,而没有其法律涵义的详释,总是觉得词不达意,不得要领。甚至于,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现在看来很是荒谬的错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Asylum”,这个意为政治庇护权的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我国1954年宪法中将其错译成居留权,一错30年,途经1975年、78年、82年三次修宪未有察觉,直到1985年修宪时才终得以纠正。年轻的薛波意识到了缺失基本法律英语工具书暗含着的风险,我们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用基本词汇、基本概念为基筑造起来的制度大厦,会不会终有一天因地基里隐藏着的无数蚁穴而轰然倒塌?! 《英汉法律词典》的发愿便在这样的环境和思考中萌生了。薛波与时任司法部教材编辑部副主编,并同样对法律英语工具书的缺失充满了担忧的闫欣达成了合作,随后及成立英汉法律词典编纂工作室,一切工作顺次展开。1995年与外文出版社签订合同,由于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薛波很是“勇敢”地约定:一年之后完成交稿! 93年至95年间,薛波同时还与外文社合作编写了《汉英法律词典》,该词典于95年出版。薛波“一年交稿”的乐观估计,就是奠定在这个基础上的: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汉英”,那么把“汉英”颠倒过来,不就是“英汉”了吗?然而,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深入,出乎意料的困难竟将真正的出版日期延长至了十年后的2003年5月。“汉英”的工作是立足于中国法律制度,把中国本身的法律条文断成术语,再翻译成英文法律词汇,只需做简单的词条搜集和编译工作。但英汉词典的制作,却需以国外法律为基准,撇开对英语系国家的法律完全陌生不说,所搜集的英文材料反映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同样是英语文献,却有来自美国的、英国本土的、马来西亚的、印度的、甚至非洲国家的,致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全然不同,换一个语境又总会看到其他语境下看不到的词汇。90年代初期,我国对英美法尚还知之甚少,薛波自然也难以知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更无从知道在西方国家哪些资料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最初他们以没有经过很多甄别的五本国外出版的英文词典作为蓝本,把每个字母系的单词分门别类、复印之后重新装订,在编译每个词目的时候都要对照五个词典中的表述综合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每本之间出入都较大,于是又往外拓展参考文献。直至阅读了大量文献,购买的书籍资料累计已达数十万元之后,他们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法律英语有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达,并且更主要的还是反映了英美法系的内容。运作至此,时间就已经过去三年。 当薛波斟酌词典是否也应当以表达法系为根本之时,他注意到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编纂、并经数次修订的《英米法词典》,其中搜集的就是纯粹的英美法术语。这一发现使他更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所有的思维和行动都应定格在这,用英汉的方式表达英美法的内容。词典的名称也最终确定——“英美法词典”,英文名为“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Anglo-American Law”。 (二)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 重新定位后,最初的一批稿子几乎全部推翻,割弃掉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英美法内容的词条,重新整理,重新起步。薛波与外文出版社的合同不得已一次次延期,关于词典的花费也难以遏制地增长。经费紧缺,工作陷入窘境,月末常常都是电话被停机之后四处筹一点钱再重新开机。薛波、闫欣不得不尝试各种方式寻找援助。他们走访了几乎所有当时较为著名的企业、律所、科研机构,找过拍卖公司争取拍卖冠名权,去涵英国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国外基金会,甚至还专门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寻求支持。为了节省邮资,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除了在工作室做编译,薛波的工作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外奔波,下雨天就把湿了的鞋放进包里,看到路边不断闪过的商标、广告,他总会习惯性地联想到:那会不会就是可以去寻找的希望? 然而社会对这部词典表现出了冷漠,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最后《北京青年报》攥文为他们谋得捐款20多万元,美国福特等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外文出版社预付稿费40余万元。至词典出版之前,薛波以个人名义在外的借款已达40多万元。 经济的拮据并没有使薛波有所退缩,社会的冷漠也并没有使他灰心丧志。薛波抖起精神与不断涌现的困难打起了“持久战”。英汉法律词典编纂工作室”此时已更名为“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室”,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位于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里的3号楼,如今该楼已经变更为女生宿舍,这一间独特的陋室在其中俨然是独具风景。推门而入,四壁图书,中立书架,书架下紧靠书桌,留下两条过道虽只能容纳一人穿梭,却能伸至屋内每一位置。至于壁架、书架可利用之处也统统都不令其闲置,钉一个钉子就能挂目录、备忘录,贴一张条还能指路,这些条的功能就如同大办公楼里的门牌,只不过办公楼里分出的部门,在这里都压缩进了这10平米之内。把剩下的空间填满,最多还能容纳10个人同时工作。置身其中,一眼就能看出,能把空间利用得如此充分,显然不在一朝一夕的功夫。 薛波的背后,还有一个虽名不见经传,却十分强有力的团队。工作室前前后后共留下过280多人伏案工作的身影。除了部分法学专家,其他多数是从政法大、北大、人大等法学院招聘而来做兼职的学生。他们全情投入,废寝忘食,有时因工作忘了时间,楼门锁了,只得从二楼的窗口跳出来,有时索性就在书桌上一睡就是一晚上。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金海军老师,加入的时候还是人民大学的本科生,之后升入硕士、博士,留校任教,对词典编纂工作却一直不离不弃。回忆起过去的时日,他只用了一个词来表达——“餐风沐雨”。这里也时常回荡着争论的声音。面对一个词汇时各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由于大家对英美法都不够熟悉,也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总结出一些“形而下”的标准:一是要语出有据,所做的词条内容和所发表的意见都必须是在地道的英美法中所表述的东西;二是尊重专业,根据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做分工,在有争议不能协调时,也以该专业的人的意见的为准。即使这样,有的问题也仍然很难解决,比如有的词条不仅涉及民商法内容,还有关诉讼法,综合性很强,常常几番争论下来都难以有结果,也只有在日积月累中慢慢解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词典就是经过不断碰撞的结果,一个词解释的程度、高度就代表了团队对这个事物认识的过程和高度。 还有一群德高望重的东吴老人,在薛波的情感中占据了最凝重的那一部分。东吴大学法学院于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的研究长期停顿,英美法教育更是因此断档了几十年。在薛波为找不到合适的审稿人之际,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词典的总审订人潘汉典先生指点,薛波前往上海,一家一家地叩开了这些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接受过系统英美法教育的老人的房门。然而老人晚年的境遇却深深震撼了薛波。东吴大学被撤销后,对东吴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后来虽得到平反,但至今许多老人晚景凄凉,多年都再未从事过与法律有关的事。被誉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先生,晚年生活在破旧阴暗的木质楼房中一间十余平米的小房间里,惟一值钱一点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他年过九旬,双手高度颤抖,只能委托80多岁的夫人来誊写改正后的稿件。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是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他的家里,惟一的电器是一台巴掌大的电扇, 90多岁的他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来审阅稿件。辛勤地工作,却几番叮嘱薛波不要署名,就连600元的微薄审稿费也捐给了编辑部。 蔡晋先生,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晚年与儿子、孙子孙媳三代共处一间小房中。重病缠身,在病床上亲自审订了49页稿件。当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终于溘然长逝。这样的事例,在薛波来往京沪之间的30多趟里,充斥着他的眼目,也沸腾了他的血液,令他在困境里一次次振作前行。体弱多病的耄耋老人,为了被摧残、埋没得太久的生命能在逝去之前再美丽地绽放一次,为了能将自己的才学汇入蜿蜒流过的文化长河、不致磨灭,他们用自己虚弱的体力、坚韧的毅力和强大的灵魂,为英美法词典的完满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薛波的一封信中,他如此写道:“从道义上我们收入了太多本不当属于我们的挚爱,尽管它已化作一份份寄托溶入这套崎岖的卷宗。” (三)“只有翻译家掌握这种技术,要领会外国语言真正的要义,要用本民族的语言表达出来,要表达得不失去本色。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过程,但比翻译家更刻板,允许我们变化的空间更小,允许想象的程度更小。”——薛波 关于词典编纂,薛波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摸索”。因为不懂,因为没做过,也因为没有人做过。他们曾经专程拜访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大家公认词典做得比较好的出版机构,但听到的总是“我们也在摸索”之类的话。我国对英美法的研究确实太过稀缺,薛波如同走进一片荒芜的旷野,材料缺乏,也探寻不到前人的足迹。“没有前辈,没有经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最基本的工作是要确定参考蓝本。但由于不了解英美法,就很难确定哪些文献是最能代表英美法、在英美法国家最具权威的。摸索了至少三年,才明了美国的布莱克词典在英美法系中的地位。 庞杂的词目中,哪些是英美法的精髓,应该重点予以阐释?哪些意义不是那么重大,可以从简带过,甚至根本不需收入?没有标准,只能自己摸索。常常是一个词洋洋洒洒、千言万言,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到后来却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它的背后还有意义更重大的词,于是又做删减;有的词原以为可以省略、从简,慢慢又发现它其实有着深远的内涵,于是重新补充。反反复复,渐渐才成体系,人力、时间也都耗去不少。 编译过程中,中国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也突出的显露出来。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与我国相去甚远,有些制度在我国是没有的,相应的法律术语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到对应词,很难用合适、贴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薛波将英美法总结为“流动的、活跃的”,总是处于快速发展、变动中。而词典又必须是确定的,越确定越便于读者理解。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或者做的也只是简单的转译、对译,就是因为这之间的鸿沟太难以跨越。难,并没有让他放弃。在不断摸索中,他们掌握了一些巧妙的技术,谓之“以静制动”。在材料中找相对最确定的部分,丢弃相对活跃、对本身的含义不重要的部分。当然,这个“找”的功夫,定然也是经过了日日年年的锤炼。 词目搜集、编译完之后,还有编辑的问题。5万多词条,相当于日本《英米法词典》收录的3倍,怎样在合理的篇幅里以最系统、最协调、最经济的方式排列出来?薛波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编辑工作的“细”——引见。我们经常会在词目的后面看见“见××页××词”的字样,以表示对该词的理解可以参见另外一个词的解释。这就是一个要把全篇的词都统一综合,再合理联系起来的过程。然而,把这么厚的材料从头至尾看一遍需要两年,不说时间的有限,即使真的有人这么看了,等他两年之后看到末尾,前面的也早已经忘却。分工负责是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每个人看一至两万个,这导致词典的某一部分是统一的,但总体而言还不够周全。对此,薛波寄望于读者和社会的力量,“一辈辈不断地进行修订、完善,也许若干年之后才能使我们的遗憾消除,达到恰如其分、完美无缺的境界。” 数不胜数的细节。每个细节都竭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考虑、去钻研,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又有新的细节出现,不断的追求着完美。而与这种追求始终形影不离的,是物质条件的极度窘迫。 “坚持是一种非常难磨的心理,不知道什么叫终结,不知道何时天亮,只有去忍受。”“不去追求可以,两年完成也可以。但真的不想,不能割舍,然而自己的能力、时间又有限。很痛苦。”薛波将自己的痛苦归结于他“对追逐细节的顽固”,但正是因为他的顽固,我们今天才可以说:《元照英美法词典》不仅仅是一本词典,它还确立了一种词典编纂的制度!